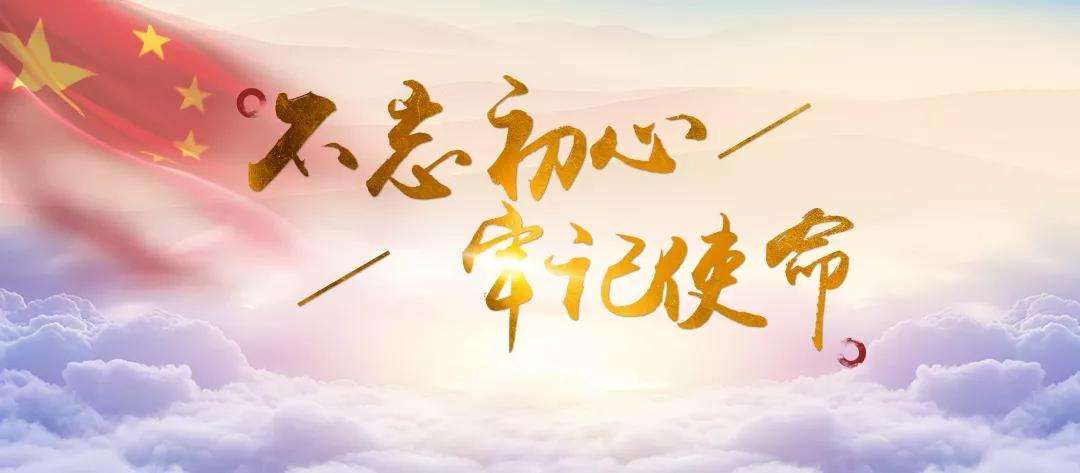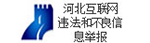記者丨曉敏 見習生丨 高原
出品丨鰲頭財經(theSankei)
在2021年10月以前,數字藏品還叫做NFT,NFT的火爆也是從2021年開始的。彼時NBA金州勇士隊的當家球星斯蒂芬·庫里就曾花費18萬美元買了一個猿猴頭像,這個頭像便是NFT,隨著越來越多的明星、藝術家的加入和資本助推,NFT一時風光無兩。時間回到現在,或許是為了強調NFT的藝術收藏價值而非金融產品價值屬性,國內的平臺對于NFT有了統一口徑的新名稱——“數字藏品”。再來看看全球最大的NFT交易平臺opensea,在這個月剛剛宣布裁員20%,“隨著加密貨幣價格暴跌和更廣泛的經濟不穩定,該行業將出現長期低迷”opensea的CEO戴文·芬澤在推特上表示。根據The Block Research數據顯示,今年6月份NFT的月度交易量只有10.4億美元,環比下降了74%。國內卻是另一幅景象,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的數字藏品平臺有近700家,此前螞蟻集團聯合敦煌美術研究所發布的售價9.9元的8000份NFT付款碼,如今在二級市場已被炒至1.5萬元以上。
數字藏品火爆 “暴富神話”引人入局
數字藏品是NFT在國內的叫法,所謂NFT就是非同質化代幣,是一種類似于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數字賬本技術,但NFT由于非同質化的特性可以用來代表獨一無二的東西,這與藝術收藏的唯一性、稀缺性相符合,數字藏品并應運而生。國內平臺對于數字藏品的入局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騰訊(00700.HK)、字節跳動、小紅書等多家互聯網巨頭先后進軍數字藏品市場,從起初的通過小程序,再到推出獨立APP。螞蟻集團的鯨探、騰訊的幻核、京東的靈稀,以及唯一藝術、IBox等平臺,目前國內數字藏品的交易平臺已經超過700家。目前國內的數字藏品平臺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無法進行交易、轉贈的平臺,如騰訊的幻核、京東的靈稀;第二類是對于轉贈有嚴格限制的平臺,如螞蟻集團的鯨探,盡管其對于轉贈有持有天數的限制,但仍存在用戶私下交易的可能;第三類便是為數眾多的對于交易不加以限制的平臺,用戶甚至可以在平臺內進行寄售。“藝術品具有收藏屬性也具有交易屬性,數字藏品也不例外,甚至入場的玩家更看重后者,畢竟已經有不少暴富的神話產生,但暴富的畢竟只是少數,當泡沫破裂時,更多數的人面臨的是血本無歸。”數字藏品玩家李焱告訴鰲頭財經。以iBox平臺為例,其7月1日發售的“二十四節氣”作品首發價格為19.9元,經歷了近20天的賣出買入,現在的標價為5195元,更早之前的“大話西游之金箍系列”藏品,首發價格為99元,但在二級市場,已被炒到了超過2萬元。
“一開始是看到朋友在玩便入了場,但我入場時已經錯過了紅利期,往往只有首發的原價產品具有較高的升值空間,但在一些平臺老用戶具有首發產品的優先購買權,新入場的玩家只能在二級市場買入賣出,這個過程就很看運氣了,我入圈兩個月下來虧了將近三萬塊。”李焱說道。
誰在助推?
數字藏品火爆的背后的推手是誰?嚴格來說,數字藏品的背后并沒有一個大莊家掌控全局,數字藏品遵循著發行方-代理機構-平臺方-買家用戶-二級市場這一鏈路,在這一鏈路上的每個環節都起到了助推的作用。“發行方通過將作品授權給代理機構,代理機構將藏品交付平臺上鏈,用戶在平臺上購買數字藏品,再通過平臺或其他渠道進行二級市場的交易,發行方一般為藝術創作者或藝術品權益所有方,代理機構又都是知名的藝術收藏機構,加之平臺方背后的大廠背書,這一鏈路看似有保障,但最終爆雷的風險全部在購買者身上,尤其是現如今藏品和平臺良莠不齊的情況下,購買者承擔著很大的風險。”互聯網行業分析人士向鰲頭財經表示。搭建一個數字藏品平臺并不難,鰲頭財經通過百度找到的一家數字藏品平臺搭建商表示,制作一個包含合成藏品、轉增、寄售、盲盒等功能的App價格在12萬到18萬不等,后續的維護費用在一年2萬到3萬之間。對于動輒幾十倍、上百倍的利潤而言,搭建數字藏品平臺的成本極低。搭建平臺,炒作藏品、攜款跑路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今年6月底,數字藏品發售平臺予藏已發布公告宣布關停業務并將進行清退。在消費調解平臺黑貓投訴上以“數字藏品”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得到一千多條條結果,涉及hotdog、One、得藝、藍貓等眾多數藏平臺,大多投訴多于平臺跑路,無法提現有關。對于數字藏品的亂象已有相關文件加以規范。今年4月26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等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NFT相關金融風險的倡議》明確提出要杜絕NFT金融化風險;同一個月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元宇宙產業委員會發布《關于規范數字藏品產業健康發展的自律要求》,建議抵制無序炒作,引導理性預期,引導平臺和發行企業應對數字收藏的合理定價,避免過度定價,避免出現嚴重泡沫。“從國家的角度來講,不愿看到大量資金游離于監管之外進行炒作,這容易引發金融風險,從之前的炒鞋、炒盲盒再到現在的數字藏品,政策的態度很明確,堅決抵制金融化,防范金融風險。”前述分析人士表示。現實則是已出臺的文件大多為倡議性質或行業自律性質,更為嚴厲的監管措施還未來到,仍有人投身于其中。
數字藏品風險重重
入市需謹慎
數字藏品面臨的不止政策上的風險,由于我國數字藏品還處于初始階段,各種問題、爭議層出不窮。版權是一方面。今年5月29日,徐悲鴻美術館在社交平臺發布版權聲明指出,某些數字平臺以徐悲鴻先生的名義為噱頭發售相關數字藏品,這些數字藏品的原始作品有些為假冒作品,有些不能提供完整的溯源證據,有些作品與徐悲鴻先生根本無任何關聯。
“某些”平臺指的則是騰訊的幻核,隨后幻核作出回應稱“幻核一直堅持合規合法原則,每期發售都檢查過合作方授權鏈路的,本次徐悲鴻藏品也是如此。我們發布的不是徐悲鴻美術館的作品。由于徐悲鴻先生過世已超過50周年,所以拍賣所得的擁有者具有獨立授權來跟幻核合作的權利。”鰲頭財經發現,鯨探、數字貓、芒境等平臺均有徐悲鴻系列數字藏品,這些藏品也取得了徐悲鴻美術館的授權,平臺方和授權方版權明晰尚且如此,一份實體藝術作品動輒生成成百上千份數字藏品,購買其中之一的消費者又獲得了怎樣的版權歸屬?文物資源和藝術品在數字版權的歸屬界定上目前仍存在邊界不清的問題。平臺與技術是另一風險,與opensea發售的NFT產品采用公鏈不同,國內的平臺出于合規考慮往往使用聯盟鏈,屬于私鏈的一種。和公有鏈相比,聯盟鏈為部分去中心化,擁有比公鏈更快的交易速度和更低的成本,但不同的聯盟鏈之間無法相互驗證。簡單地說,用戶在螞蟻集團的鯨探上購買的徐悲鴻的馬,并不能轉移到騰訊的幻核之上。“聯盟鏈數字藏品的收藏價值并不如公鏈的大,如果一些小的聯盟鏈跑路或停止運營,用戶則會找不到其購買過的藏品。”區塊鏈行業觀察人士向鰲頭財經表示,“聯盟鏈的最大意義在于防范金融風險,用戶無法獲得秘鑰,想要交易就必須依賴平臺獲得技術支持,而在公鏈如opensea上購買NFT直接獲取私鑰,并將其任意掛出銷售。”對于數字藏品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火爆的背后,很難說清是真有收藏價值還是資本的擊鼓傳花游戲,即便是后者,身處這場游戲中的人也都不會,也不愿相信炸彈會在自己手上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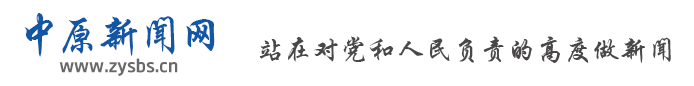
 0310-3111082
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3047798688@qq.com